提交成功
共1条医生回复
因不能面诊,医生的建议仅供参考,具体诊疗请一定到正规医院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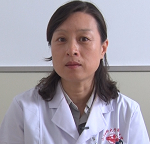
-
朱亦堃主任医师
病情分析:请不要卵西方医学家的之口诬蔑中医请不要卵西方医学家的之口诬蔑中医一位名叫周东浩的先生,近来连篇发文,势头很盛。但他动辄以西方人的立场和观点评判中医的是非成败,本人不敢苟同。泰山和东海,各擅胜场;春兰和秋菊,别具芬芳。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互相否定。西医有西医的特点;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蓝眼睛黄头发是一种风景;黑头发黄皮肤也别具神韵。各方应该相互学习和交流,不要相互攻讦和诋毁。千变万化,千姿百态才成世界,千人一面,一成不变并不符合自然规律。周先生说,中西医学的另一不同点: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明眼人一望可知,所谓“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是西医的学说,中医理论中并无此内容和说法。中西医在这方面根本没有可比性,无法以此来评判谁优谁劣。譬如讲龟兔赛跑,是因为龟和兔子都具有行走能力,速度却大不同。而如比较兔毛和龟甲的优劣,则失去可比性。龟甲是乌龟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兔子则毫无意义;但您不能说因为兔子不需要,就认为龟甲无用或低劣。反之也是一样,不能因为乌龟不需要兔毛,就否定兔毛对兔子的重要性。同样的道理,不能因为中医不讲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就认为中医没有西医先进或其他什么的如何如何。至于大讲什么“西医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建立在神经调节基础上的,而中医则更重视体液调节。这是中西医学的又一重要不同。”更是信口雌黄!什么时候中医理论中有过体液调节学说?中医理论中从来没有过诸如肾上腺皮质激素之类的概念和名词,怎么就突然冒出了体液调节?至于所引用的西方医学家所说的一段话:西医是“唯头脑的医学”,中医则是“无头脑的医学”。这段话看似是一般的调侃之词,实际上是对中医的诬蔑之态跃然纸上。中医学中对头和脑论述深刻详备,只是那位西方老外毫不知晓罢了。他在那里胡说什么,是他的自由,也不足为怪。而作为国内人甚至中医对此懵懂无知。还不遗余力地对西方老外吹捧直至,实在可笑,可悲,可叹!从考古发掘的甲骨文上记载的疾病和医药卫生活动可以得知,祖国医学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存在。由此以降,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医药学经历着自然环境的变迁和历史社会沿革,一直和我国人民的健康事业息息相关。中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同各种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历代医家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历史唯物认识观,发扬“医者仁术”和“痌瘝在抱”的救死扶伤精神,在对“巫医”、“巫术”、封建迷信以及各种歧视中医思想的不懈斗争中,顽强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时至今日,在我国乃至世界医疗卫生体系中,中医学仍以其实践的普遍有效性和较佳重复性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医学是世界上单独有着5000年连续历史的,独立于西方医学的医学。其至今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它植根于中华文化,其中贯穿的是以《易》学思想为基本格局的“象”思维模式。以“象”为认识基本层面的思维,强调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去认识事物现象本质。由于世界的纷繁复杂性和变化随机性,导致这种思维**依靠经验的总结、归纳和推演,因而是抽象的。国内传统“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世间万物生长于自然环境之中,无不受到其影响,各种生物的生老病死莫不与其相关,人类与自然同样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中医学通过观察机体的总体状况,不孤立地看待疾病本身,在“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指导下,动态的寻找疾病的规律,以对“证”下药。2003年的SARS疫情蔓延全球,西方科学家致力于找到一种**药物和疫苗杀死“冠状病毒”。中医无法也没有努力找出致病源,但是根据时间、气候环境、病邪的属性、个体差异、证候表现进行辨证论治,针对时、地、人这一宏观现象进行预防与治疗。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治疗60例“非典”患者,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达到3个“零”的奇迹。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治疗80多例,其中中医介入治疗者71例,但这71例中,死亡者仅1例。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纯中医治疗16例,也无一例死亡。而且凡是用中医介入治疗、激素用量少的“非典”患者,至今观察未见有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后遗症。事实证明中医防治SARS效果胜于西医,已可定论。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形势和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潜在的危机。其中有中医界本身的问题,也有中医圈以外的质疑。主要的辩论集中在“中医是否具有科学性”、“中医是否能看病”、“中药的副作用”等等问题上。这些问题但凡是关心热爱中医的人,抑或是反对抵制中医的人都很关注,围绕这些焦点做了很多文章。他们的观点笔者不愿擅加评论。由于“科学与否”是作为现代人们衡量事物好坏的单独标准,中医的是否科学即是中医生存或消亡的理由。尽管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仍旧需要再啰嗦几句。“中医不科学”是莫须有的罪名“科学”的英文“Sciece”,原意为“知识”、“学问”。乾嘉年间传入国内后,我国学者根据《礼记?大学》中“格物而后致知”(意即通过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将Sciece译为“格致”、“格知”。明治维新时,日本学界认为Sciece是指“分科的学问”,故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将其引入国内,而后才逐渐流行起来。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民主与科学的象征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全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国内近代史上是有很大功绩的。但稍微有一点偏激,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国内传统文化全盘拉下马。中医药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受到“牵累”。毛嘉陵先生在《东方有科学》一文中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以说明那个时代的崇尚“科学”,反对中医的“风尚”。“1926年3月,新文化运动大师梁启超因血尿,被协和医院动手术割掉了没有病变的右肾,由此引起社会很多议论。尽管梁先生后来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仍然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为协和进行了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国内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这虽然显示了梁先生的宽广胸怀,但对这样一个明显的医疗事故也不予承认,即使自己被错割了一个肾,还要如此‘辩护’,同时也不忘批判中医药,这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精神?”了解中西医学论战史的人都会记得早在上世纪20-40年代,以余云岫、傅斯年为首的废除中医派,公然提出了“废止中医”等提案,他们甚至不屑称祖国的传统医学为中医或国医,而贬称之为“旧医”。丁兆平先生说:“中医的危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此期间,中西医的学理讨论溢出医学界而进入言论界,并进一步触动了政界乃至整个民国社会,饭碗问题与学理问题交织一起,学界人物与政界人物互为激荡,将一场本可以局限在学理层面的讨论闹得沸沸扬扬。”“……举国岐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国内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结果是……大家不了了之。”其争论的实质就是中医的科学性问题。诸如“中医科学性质疑”这类的陈仓烂谷,至今仍然在模糊和困扰着一些人们的思想认识。由于中医药历史的“传统”和“古老”,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在一部分现代先生的思想观念中也很容易自然不自然地把中医药与“落后”、“不科学”甚至“风水”、“算命”联系在一起,将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对立起来,“崇洋媚外、重西轻中、中医落后论、民族虚无等错误思潮,还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的存在。”在国内改革开放进程遇到困难,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果断的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单独标准”。不管是中医、西医,能看好病就是好医。中医是看病的学问,评判科学性的时候还是让疗效说话。客观地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和自然顽强抗争的斗争史。自东汉以下,发生了难以计数的大规模瘟疫,始终是中医无数次的拯救人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人们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无私的贡献。如果中医没有疗效,治不好病,她就根本无法延续到现在。及至当代,中医药防治乙脑”、“流脑”、“甲肝”以及SARS等传染病仍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实践”证明中医是“真理”!中医的不“科学”是人造成的前一段时间,有人在中医报上刊出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优秀学者章太炎曾经赞扬张仲景的学术。章氏认为,张仲景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家,是因为他的《伤寒论》中将五行的旧思想加以抛弃,具有革新精神,独辟蹊径。乍一看,似乎在理。与老师讨论这个问题,老师淡然一笑,张氏在其《伤寒论》书序中明确提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伤寒论》中也许没有五行的原字,但其中贯穿的思想,无不宗法“阴阳五行”。像章太炎这样的大学者,没有对中医深入的研究,凭卵直觉经验判断,导致犯下这样简单逻辑错误,尚可原谅。可是作为报社编辑,专业人员,居然将此类文章标新立异,未免有失“科学精神”了吧!邓铁涛老先生说:“中医是不是‘科学’至今已争论一百多年了,遗憾的是现在有些高学历、高年资的‘中医’也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据我观察,对中医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大多数是脱离临床的,或者是以西医学指导临床的。因其脱离中医临床,或不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因此无法印证中医理论之正确与可贵。”“不是中医学不行,是学中医的人不行。”这句话深刻的道出了当今中医艰难处境的原因。现在从中医院校学生的培养模式到研究方向无一不是按照西医教学方法亦步亦趋。中医学硕士,甚至博士研究生,不会开一张像样药方的人大有人在。中医博士的案头放着一本《黄帝内经》是要被人当作笑料的。大批中医院校的研究生作为高级中医接班人,却在分子生物学、基因芯片等高科技领域艰难“摸索”。这些努力本是无可厚非,但其成效与往往与先期投入难成正比。毕竟是背了几年汤头的人了,想要在一两年中有所创举,非常人力可为也。再一个就是几乎所有的临床专业的研究生都在作药物的疗效分析,换句话说也就是药理学、药效学和药代动力学的研究课题。所做的“实验”并非是“试验”,最后“数据”的来源是多种渠道的,先有结果后作试验,数据编造抄袭种种现象屡见不鲜。(这种趋势流行的另外一个原因——这些试验的收入比较可观。)每年国家投入中医研究的经费大多用于此类项目购买实验仪器、动物以及试剂等等等等。相反,真正探求中医理论,潜心临床的人寥寥无几,投入基础研究的资金更是相形见绌,捉襟见肘。仅从历年报考研究生的专业生源比例来看,像基础理论、医史文献这类专业往往出现零**的现象。有人说,“肉包打狗”型的专业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理论的。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中医理论的失传,技术的滞后和学术的衰退。中医的阵地失守,西医就必然占据上风。(这里并非在强调中西医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用西医学的理论指导中医是“废医存药”的观点,即认为中医无医理,按照西医理论指导中医治疗和中药应用。早些时候《国内中医药报》上的一篇文章披露了“清开灵”注射剂的临床副作用及相关问题,正暴露出西医理论在指导中医用药的思路上是完全走不通的。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可能当今中医界的状况不至如此,但前闲明训仍当永铸心中,以免危若冰谷!中医不叫科学又如何“中医完全没有科学依据。”试问什么是科学?我的认为,“科学”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凡是能被科学解释合乎逻辑的、现代的、甚至**的一个概念。即现在的通行观点就是“正确”、“合乎常理”的代名词——这种观点的衡量标准是西方的科学。抑或不是,而仅是某些先生的经验猜想和主观臆断。按照此等标准,阴阳、五行等等中医概念无一合乎其“科学”理论。科学能够解释一切吗?科学解释不了的都不科学吗?经验和臆断能够代替实践吗?相信多数人会赞成这种观点——在探索自然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相信与质疑同等重要,当无法找到推翻假证的确切依据时,就不能想当然地指责是不科学、伪科学。如果那些自认为掌握现代科学的先生们执意要把中医从科学的阵营中赶出去。那么,中医不叫科学又如何?中医药学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史,是经过无数临床人体实践检验的可重复性的医学。在默默无闻为我国人民服务几千年后,曾几何时,中医药学却被来自西方的几百年历史的文化冲击的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可悲的是这股逆流的排头兵居然是国内人自己。中医药学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其顽强的延续并完善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以期达到更好的临床效果。简单的说,中医是在治病人。中医学重视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心理影响以及个体差异等等相关因素的与人类疾病相互关系。在养生时提出“顺应四时”、“道法自然”,注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与“天地四时相应”;在辨证中提出“整体观念”、“审证求因”,根据“四诊合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以及“三焦辩证”、“气血津液辨证”等多角度,交叉立体辨证方法,以求辨证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和结合;治疗中讲究“辨证论治”、“理法方药”、“急治其本,缓治其标”、“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理论,总结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以及“虚则补之”、“劳则温之”、“寒则温之”等等具体的具体临床指导原则。在中草药学方面,无论从原始社会“神农尝百草”到“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性味归经”等一系列中药理论的形成,以及“君臣佐使”、“十八反”、“十九畏”等方剂和药物配伍禁忌的理论原则的完善,还是对中草药的“种植采集”、“加工炮制”等都归纳总结出一整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中医药学是国内人民智慧的结晶,它以其系统的理论源流、独特的临床疗效和民族的文化气息巍然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过去的数千年中,中医药学拯救苍黎于无数灾疫之中;将来她同样会协助人类战胜一个又一个病魔,为人类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前几年韩国经济困难时,听说韩国人坚决抵制日本家电、汽车,坚持用国产商品以支持本国经济的发展;近来又听说韩国在替首都“改名”,因为“Seoul”这个韩文向来都没有音、义匹配的中文字,加上用“汉城”的“汉”字,让人联想到国内的汉朝,故当局有意更改译名。由此,韩国人的民族自尊意识之强烈可见一斑。在中医发展追求科学化、标准化而逐渐失去中医本色的时候,在中医未来发展方向出现分歧难以抉择的时候,坚定的中医人,你何不找回自信,挺直脊梁,张臂疾呼:“中医不叫科学又如何?”
查看更多关于“中西医有何区别”的相关常识>>








